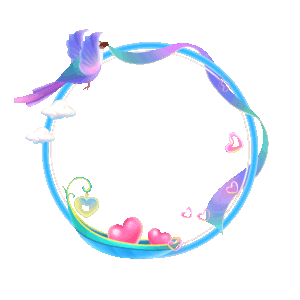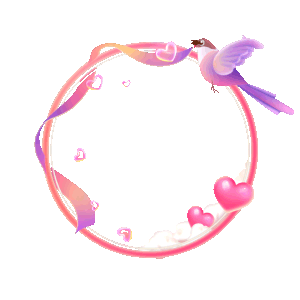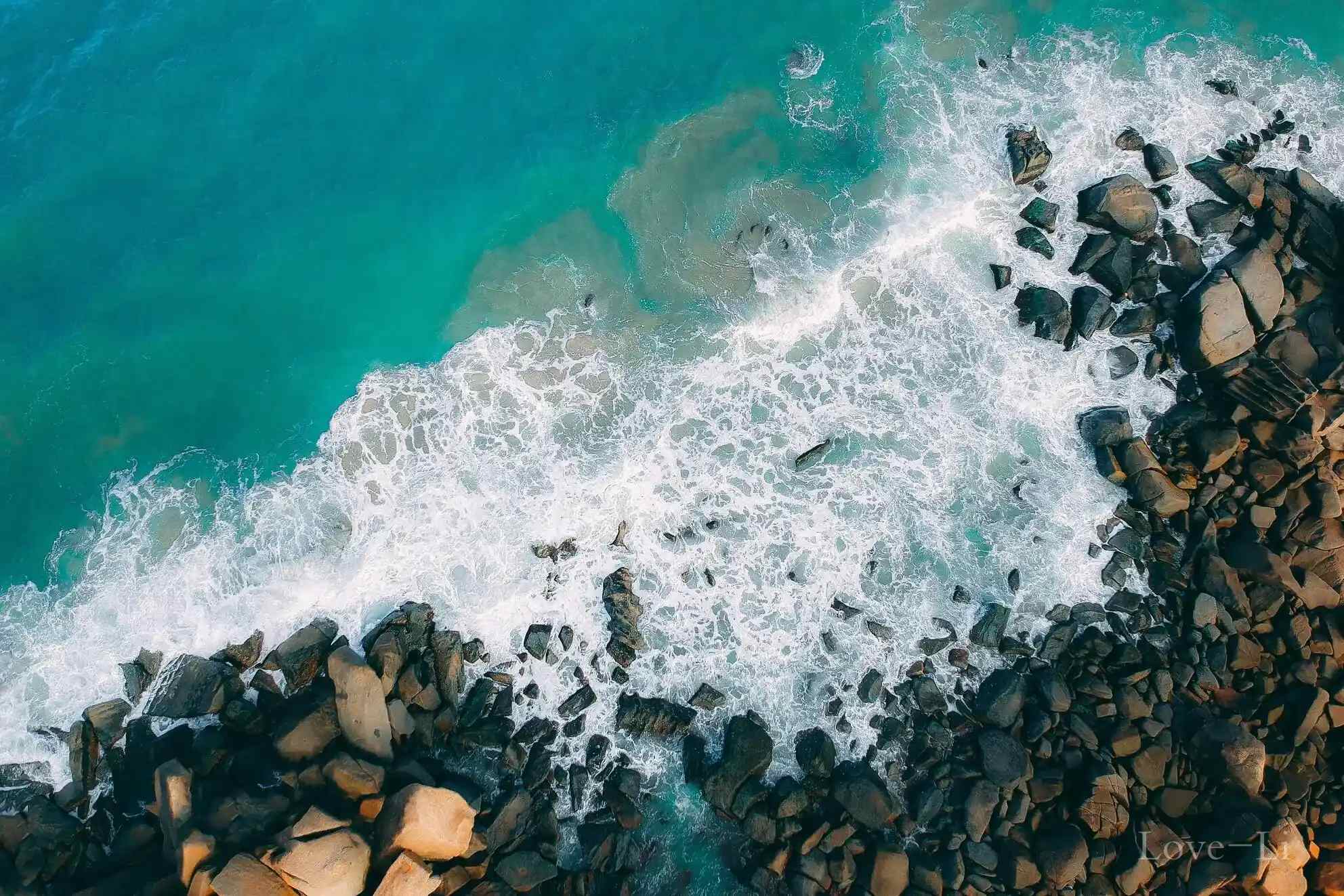七月二十一日的傍晚,暑气尚未完全褪去,蝉鸣仍在梧桐叶间此起彼伏地喧嚣着。我们站在影院玻璃门前,影子被夕阳拉得老长,交叠在一起像是某种隐秘的约定。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看电影,选的是《长安的荔枝》。检票员撕下两张票根时,我的掌心微微沁出汗意,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那张轻薄的纸张,仿佛触碰到了什么易碎而珍贵的东西。
影厅里的冷气裹挟着爆米花的甜香扑面而来。我们挑了中间靠后的位置坐下,座椅皮革还带着白天阳光烘烤后的余温。幕布亮起前的那几分钟格外漫长,黑暗像温柔的水慢慢漫过脚踝、腰际、胸膛,最终将我们彻底淹没。她的头发扫过我的手臂,发梢残留着柠檬味洗发水的清香,我听见自己剧烈的心跳声混进空调运转的嗡鸣里。
影片开场的画面是长安城的飞檐斗拱,青灰色瓦片上跳跃着细碎的光斑。故事随着一骑快马奔向岭南展开,马蹄扬起的尘土掠过官道两侧开满野菊的田埂。当镜头切到贵妃轻咬荔枝的特写时,李冉忽然轻轻捏了捏我的手背——她总是这样,看到动人处便忍不住要与我分享震颤的神经末梢。黑暗中我们的手指自然扣在一起,她的指甲盖涂着浅粉色的珠光,像落在掌心的星屑。
电影里的杨刺史策马穿越崇山峻岭时,荧幕外的我们也正经历着相似的跋涉。那些辗转千里运送鲜果的细节,被导演拍得像一首绵长的叙事诗。我看见李冉睫毛投下的阴影随着剧情起伏颤动,有时眼眶里蓄满泪水却不掉落,就像挂在荔枝树上将落未落的晨露。散场灯亮起的时候,她侧脸看我,眼底映着屏幕上滚动的演职员表,恍惚间竟觉得她比银幕上的任何角色都要鲜活。
走出影院时已是华灯初上。晚风掀起李冉的裙摆,她转身冲我笑,路灯把她的影子剪成跃动的剪影。“原来古代人也这么拼命送外卖啊。”她开玩笑的语气里藏着认真,“不过能送到宫里,也算值得了吧?”我望着她被夜色染成琥珀色的瞳孔,突然明白有些奔赴确实值得——比如此刻并肩走在夏夜街头的我们,比如方才在黑暗中相触的体温。
路过便利店时买了两支冰棍,撕开包装纸时腾起的白雾模糊了彼此的脸。咬下第一口的瞬间,清甜的凉意直窜天灵盖,像极了电影里竹筒保鲜法带来的惊喜。我们踩着斑马线上斑驳的光晕往家走,谁都没有提下次要看什么片子,但都知道这样的夜晚不会只有一次。
后来回想起那个晚上,总觉得奇妙。明明是去看别人的故事,却在光影交错间照见了自己的影子;本该专注银幕的时刻,余光却总忍不住描摹身旁人的轮廓。或许爱情就是这样一场双重曝光,把两个灵魂的底片叠印在同一张胶卷上。而我们的第一次,恰好定格在荔枝成熟的时节。